諾姆·杭士基
艾弗拉姆·諾姆·杭士基(英語:Avram Noam Chomsky[b];1928年12月7日—),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認識科學家、史學家[c][d]、社會批判家和政治活動家,有時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e]。杭士基是分析哲學領域的重要人物、認知科學領域的創始人,也是亞利桑那大學語言學系的榮譽教授和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系的榮譽退休教授,他著有150多本書,內容涵蓋語言學、戰爭、政治及大眾傳媒。意識形態方面,他是無政府工團主義和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
| 諾姆·杭士基 Noam Chomsky | |
|---|---|
 2017年的杭士基 | |
| 出生 | 艾弗拉姆·諾姆·杭士基 Avram Noam Chomsky 1928年12月7日 |
| 國籍 | |
| 母校 | 賓州大學(1949屆文學士;1951屆文學碩士;1955屆哲學博士) |
| 配偶 |
|
| 兒女 | 3[a] |
| 父母 | 威廉·杭士基 艾爾西·西蒙諾夫斯基 |
| 獎項 |
|
| 網站 | chomsky |
| 科學生涯 | |
| 研究領域 | 語言學、分析哲學、認知科學、政治評論 |
| 機構 | |
| 論文 | 轉換分析(1955年) |
| 博士導師 | 澤里格·哈里斯[1] |
| 受影響自 | |
| 譯名差異 | |
| 中國大陸 | 諾姆·喬姆斯基 |
| 臺灣 | 諾姆·杭士基 |
| 簽名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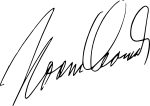 | |
杭士基出生於費城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早年在紐約市的另類書店被無政府主義吸引。他本科就讀於賓州大學,碩士期間曾在哈佛學會工作,並提出了轉換-生成文法理論,以該理論於1955年獲得博士學位。他自1955年起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並於1957年以里程碑級作品《句法結構》成為語言學界的重要人物,該作品在重塑語言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58年至1959年間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他創立或與他人合作創立了普遍文法理論、生成文法理論、最簡方案模型和杭士基譜系。杭士基成功促使語言行為主義步向衰落,並曾著力批評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的研究。
1967年,杭士基因其反戰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而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他在文中直言不諱地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並批評稱這是帝國主義的行徑。此後他與新左翼建立了聯繫,因為他激進的反戰活動多次被捕並被列入理查·尼克森總統的對手名單中。之後的幾十年裡,他在繼續進行自己的語言學工作的同時,捲入了語言學的戰爭中。他曾與經濟學家愛德華·山繆·赫爾曼合作,出版了研究媒體宣傳模式的《製造共識》一書,並致力於揭露印度尼西亞占領東帝汶時期的行徑。他為無條件言論自由及為納粹大屠殺否認論的辯護在20世紀80年代福里松事件中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學工作退休後,他繼續從事聲勢浩大的政治活動,如反對入侵伊拉克,支持占領運動。自2017年起杭士基開始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
作為在世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之一[11],杭士基影響了一系列學術領域。他被廣泛認為幫助引發了人文科學的認知革命,為研究語言和心靈的新認知主義框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除了學術方面的貢獻外,他今日仍是美國外交政策、新自由主義、當代國家資本主義、以巴衝突和主流新聞媒體的主要評論者。杭士基和他的思想在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生平
編輯童年:1928–1945年
編輯艾弗拉姆·諾姆·杭士基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東橡樹巷[12]。他的父親是澤夫·威廉·杭士基,母親是艾爾西·杭士基·西蒙諾夫斯基,二人均是猶太裔[13]。威廉於1913年因逃避兵役而離開俄羅斯帝國,在上大學前曾在巴爾的摩的血汗工廠和希伯來語小學工作[14]。到了費城後,威廉成為了以色列希望公理會宗教學校的校長,同時加入了格拉茨學院。威廉非常重視教育,希望通過教育使每個人都能「生活融洽、思想自由獨立,關注且熱心參與世界的改善和提升,使生活對所有人來說都更有意義、更有價值[15]」,他的這些理念隨後被年幼的諾姆所繼承[16]。艾爾西則是一位出生於白俄羅斯的美國教師和活動家。二人在一同工作的以色列希望公理會相識[13]。
諾姆是威廉的第一個孩子,他的弟弟大衛·伊萊·杭士基生於1934年,比他小五歲[17][18]。兄弟倆的關係很好,不過大衛的性格比較隨和,而諾姆的性格有時比較好勝[19]。兄弟二人從小就在猶太人的氛圍下長大:他們學習希伯來語,並經常一同討論錫安主義的政治理論;他們一家受阿哈德·哈姆的左派錫安主義著作的影響頗深[18]。諾姆自幼也長期與費城愛爾蘭裔和德國裔社群的反猶太主義共處[20]。
諾姆曾於獨立的杜威派橡樹巷日校[21]和費城的中央高中就讀,他學習成績優異,課餘參加各種俱樂部和社團,但他對學校的等級制度和制度化的教學方法感到不安[22]。他還曾在他父親教書的格拉茨學院的希伯來高中就讀[23]。
杭士基認為他的父母是中間偏左的「正常羅斯福民主黨人」,但參加國際女裝工會的親戚讓他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和極左政治[24]。杭士基在看望他的叔叔時,經常順道去左翼和無政府主義書店大量閱讀政治文獻[25]。杭士基的第一篇文章寫於十歲那年,文章是論在西班牙內戰中巴塞隆納陷落之後,法西斯主義蔓延的威脅[26]。從十二歲或十三歲開始,杭士基開始以無政府主義者自居[23]。發現無政府主義後來被杭士基形容為「一次幸運的邂逅」[27],他對史達林主義和其他形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持批判態度即源於此[28]。
大學:1945–1955年
編輯1945年,16歲的杭士基進入賓州大學學習,在這裡,他進一步學習了哲學、邏輯和語言學,並對阿拉伯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9]。他通過在自家中教授希伯來語補貼他讀本科的花費[30]。不過,他曾對自己在本科階段的經歷感到沮喪,考慮過退學並搬到巴勒斯坦託管地的一個基布茲內生活[31]。1947年,杭士基在他的政治圈子內與俄羅斯出生的語言學家澤里格·哈里斯相識,二人的交談重新喚醒了他的求知慾。哈里斯向杭士基介紹了理論語言學領域,並說服了他主修該學科[32]。杭士基在他的學士學位論文《現代希伯來語的形態分析》便開始將哈里斯的語言學方法應用於希伯來語上[33]。杭士基在1951年獲得賓州大學的碩士學位時對這篇論文進行了一些訂正和調整;隨後這篇論文被出版成書[34]。大學期間,他還在納爾遜·古德曼的教導下對哲學產生了興趣[35]。
1951年至1955年間,杭士基是哈佛大學學會的成員,他後來的博士論文植根於他在這裡的一些研究[36]。在古德曼的鼓勵下[37],杭士基被哈佛大學所吸引,當然也有部分因素是哲學家威拉德·范奧曼·蒯因也在此。奎因和牛津大學的訪問哲學家約翰·朗肖·奧斯丁都對杭士基產生了很大影響[38]。1952年,杭士基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文章《句法分析系統》,這篇文章並未發表在語言學期刊上,而是發表在了《數理邏輯學期刊》上[37]。1954年,他在芝加哥大學和耶魯大學的講座上對當時語言學中的行為主義思潮進行了批評[39]。他中間有四年沒有向賓州大學報道,但1955年他向該校提交了一篇論文,闡述了他關於轉換文法的想法,因此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後來被收錄進1975年出版的《語言理論的邏輯結構》一書中,但在此之前已在專家中被不斷地私下傳閱[40]。哈佛大學教授喬治·米勒對杭士基的論文印象深刻,並與他合作撰寫了幾篇計算語言學方面的技術論文[41]。杭士基的博士學位使他免服應於1955年開始的義務兵役[42]。
1947年,杭士基開始了與自幼便相識的卡羅爾·沙茨的戀愛,二人隨後於1949年成婚[43]。杭士基成為哈佛大學的研究員後,二人搬到了波士頓的奧爾斯頓地區,1965年二人又搬到了列克星敦郊區[44]。1953年,夫婦二人拿著哈佛大學的旅行補助金去了歐洲,二人從英國出發,歷經法國、瑞士、義大利[45]和以色列,在以色列,他們住在青年衛士的播種者基布茲。儘管一路上玩的很開心,但杭士基對這個國家的猶太民族主義、反阿拉伯種族主義以及在集體農場的左派社群內的親史達林主義感到震驚[46]。
杭士基常去紐約市觀光,順道光顧意第緒語無政府主義期刊《勞動者自由之聲》的辦公室。他受該期刊撰稿人魯道夫·羅克的思想影響很深,他的作品讓杭士基了解到無政府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之間的聯繫[47]。杭士基還閱讀過其他政治思想家的作品: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和迪亞哥·阿瓦德·德·桑蒂連的作品,民主社會主義者喬治·歐威爾、伯特蘭·羅素和德懷特·麥唐納的作品,馬克思主義者卡爾·李卜克內西、卡爾·科爾施和羅莎·盧森堡的作品[48]。這些著作使他相信無政府工團主義社會的可能性,他對奧威爾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中記載的西班牙內戰期間建立的無政府工團公社十分感興趣[49],並在閱讀了左派期刊《政治》後對無政府主義產生了進一步的興趣[50],還閱讀了委員會共產主義期刊《生活的馬克思主義》,儘管他不認同其編輯保羅·馬蒂克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念[51]。他還對反史達林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團體美國列寧主義聯盟的馬列主義思想感興趣,對其將二戰描述為西方資本家和蘇聯煽動的「假戰爭」印象深刻[52]。杭士基「從未真正相信這些論述,但……發現它們很有趣,足以讓人弄清楚他們在談論什麼」[53]。
早期學術生涯:1955–1966年
編輯杭士基在麻省理工學院結識了兩位語言學家,莫里斯·哈勒和羅曼·雅各森,雅各森在1955年為他爭取到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這段時間裡,杭士基一半時間用在了機器翻譯專案上,另一半時間用於教授語言學和哲學課程[54]。他形容麻省理工學院是「相當自由和開放的地方,對實驗開放,沒有嚴格的要求。對我這種特立獨行的人來說簡直就是完美」[55]。1957年,麻省理工學院擢升他為副教授,1957年至1958年,他又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客座教授[56]。同年,杭士基與沙茨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給他取名為阿維瓦[57]。他還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關於語言學的書《句法結構》,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種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結構主義學派截然不同的理論[58]。對杭士基的觀點的反應從冷漠到敵視不等,他的工作造成了語言學內的重大分歧[59]。語言學家約翰·萊昂斯於後來評論道:「《句法結構》徹底改變了對語言的科學研究」[60]。1958年至1959年間,杭士基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擔任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員[61]。
1959年,杭士基在學術期刊《語言》上發表了對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1957年出版的《言語行為》一書的書評,他反對斯金納將語言視為學習行為的觀點[62][63]。杭士基在這篇書評中認為,斯金納忽視了人類創造力在語言學中的作用,這篇書評幫助杭士基確立了他知識分子的地位[64]。在哈勒的幫助下,杭士基繼續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期間的語言學專案。1961年,他被授予終身職位,成為現代語言學系的全職教授[65]。杭士基接著被任命為1962年在麻薩諸塞州劍橋舉行的第九屆國際語言學家大會的大會發言人,這使他成為美國語言學的事實上的發言人[66]。1963年至1965年期間,他為一個由軍方贊助的,「將自然語言確立為指揮和控制的操作語言」的專案提供諮詢;該專案合作者、杭士基當時的學生芭芭拉·帕蒂說,這項研究對軍方來說是一項有正當理由的研究,因為「如果發生核戰爭,將軍們會在地下用一些計算機來管理事情,而教計算機理解英語可能比教將軍們編程更容易」[67]。
杭士基在這十年間繼續發展他的語言學思想:1965年發表了《句法理論面面觀》、1966年發表了《生成文法理論的話題》和《笛卡爾語言學:唯理主義思想史之一章》[68]。他與哈勒一起,為哈珀–羅出版社編輯了《語言研究》系列書籍[69]。隨著著作的接連出版,他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可,並得以於1966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演講[70]。他後來將這次演講編錄入1968年出版的《語言與心智》一書[71]。儘管杭士基的地位不斷提高,但他與一些早期的同事和他帶的博士生——包括保羅·波斯特、約翰·羅伯特·羅斯、喬治·萊考夫和詹姆士·大衛·麥考利——之間的分歧引發了一系列今日被稱為「語言學之爭」的學術爭論,儘管這些爭論實際上主要圍繞哲學問題而不是語言學展開[72]。
反戰活動家和異議人士:1967–1975年
編輯杭士基參加了對美國在1962年參與越戰的抗議活動,並在教堂和家庭中的小型聚會上就這一主題發表了演講[74]。1967年,他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包括〈知識分子的責任〉在內的數篇反戰文章[75],使他成為了一名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76]。〈知識分子的責任〉與其他政治文章隨後被收入杭士基1969年出版的第一本政治類書籍《美國強權和新官僚》[77]。他後來繼續出版了一系列探討政治的書籍,包括1970年出版的《與亞洲交戰》、1973年的《密室男孩》、1973年的《國家因素》、1974年的《中東和平?》[78][79]。這些著作使他與美國的新左翼運動有了聯繫[80],儘管他對著名的新左派知識分子赫伯特·馬爾庫塞和埃里希·弗羅姆評價不高,而且更喜歡與活動家而非知識分子為伴[81]。這一時期里,杭士基仍長期被主流媒體忽視[82]。
這一時期他亦開始參與左翼活動。杭士基拒絕繳納一半的稅款,公開支持拒服兵役的學生,並因參加五角大樓外的反戰教學示威被捕[83]。在此期間,杭士基與米切爾·古德曼、丹尼斯·萊沃托夫、威廉·斯隆·科芬和德懷特·麥唐納共同創立了反戰團體RESIST[84]。儘管他對1968年學生抗議的目的有所質疑[85],但杭士基仍為學生運動團體做了許多講座,並與他的同事路易斯·坎普夫一起,在麻省理工學院獨立於保守派主導的政治學系開設了關於政治的本科課程[86]。隨後學生活動家發起運動,要求停止麻省理工學院的武器和反叛亂研究時,杭士基表示了同情,但認為研究應繼續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監督下進行,且限於威懾和防禦系統兩方面的研究[87]。1970年,他訪問東南亞,在越南的河內理工大學作了演講,並參觀了寮國的難民營。1973年,他幫助領導了一個紀念反戰者同盟成立50周年的委員會[88]。
| 外部圖片連結 | |
|---|---|
| 杭士基於1967年10月21日參加向五角大樓行軍 | |
| 杭士基與其他公眾人物的合照 | |
| 示威者在前往五角大樓的途中經過林肯紀念堂時的照片 |
由於積極參與反戰活動,杭士基曾多次被捕,並被列入總統理查·尼克森的主要政治對手名單[89]。杭士基開始意識到他公民不服從行為的潛在影響,沙茨也開始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以便在杭士基被監禁或失業的情況下撐起整個家庭[90]。不過最終杭士基在科學界的聲譽使他免受其信仰的行政行為的影響[91]。
他在語言學方面的工作則進一步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這一時期他獲得了多個榮譽博士學位[92]。他在劍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史丹佛大學發表了包括伍德布里奇講座在內的多場公共演講[93]。他在1971年與法國歐陸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辯論中的表現使他被定位為分析哲學的代表性人物[94]。這一時期他繼續發表一系列語言學方面的文章,包括《生成文法中的語義研究》(1972年)[91]、《語言與心智》的一個擴充版(1972年)[95]和《對語言的思考》(1975年)[95]。1974年,杭士基被聘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93]。
愛德華·山繆·赫爾曼與福里松事件:1976–1980年
編輯杭士基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繼續出版語言學著作,一方面用這些著作理清他早期的工作,另一方面處理部分對他理論的批評並更新他的文法理論[96]。但他的政治發言經常引起相當大的爭議,特別是當他批評以色列政府和軍隊時[97]。1970年代初,杭士基開始與亦曾批評過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愛德華·山繆·赫爾曼合作[98]。他們一起寫了《反革命的暴力:事實與宣傳中的浴血奮戰》一書批評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介入以及主流媒體對其的不報道。華納模塊公司於1973年出版了該書,但其母公司不喜該書的內容,並隨後下令銷毀所有副本[99]。
雖然主流出版社大都拒絕出版杭士基的新作,但杭士基在麥可·阿爾伯特的南端出版社——一家以活動家為導向的出版公司——中找到了支持者[100]。1979年,南端出版社出版了杭士基和赫爾曼修訂《反革命的暴力》後作為兩卷本的《人權的政治經濟學》一書[101]。這本書比較了美國媒體對紅色高棉大屠殺和印度尼西亞占領東帝汶的反應,同時認為,由於印度尼西亞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媒體忽視了東帝汶的情況,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國的敵人柬埔寨的事件上[102]。杭士基的後續反應,包括在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上的兩次證詞,成功地激發了美國媒體報道占領事件,並在里斯本與東帝汶的難民會面[103]。馬克思主義學者史蒂文·盧克斯公開指責杭士基背叛了他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充當了柬埔寨領導人波爾布特的辯護人[104]。合作者赫爾曼稱,這場爭論給杭士基「帶來了嚴重的個人代價」[105]。杭士基本人則認為,「東方或西方的循規蹈矩的知識分子」處理不同意見的方式都是試圖「用大量的謊言來淹沒它」[106]。他認為對自己的批評不如「主流知識分子為自己國家的罪行辯護」的證據重要[106]。
杭士基長期以來一直公開批評納粹主義和更常見的極權主義,但他對言論自由的擁護使他為被廣泛認為持納粹大屠殺否認論立場的法國歷史學家羅貝爾·福里松的權利辯護。不過,在杭士基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為福里松的言論自由做出的辯護被作為後者1980年出版的《對那些指責我偽造歷史的人的反駁》(Mémoire en défense contre ceux qui m'accusent de falsifier l'histoire)的序言出版[107]。杭士基因此受到廣泛譴責[108],法國的主流媒體指責杭士基本人是大屠殺的否認者,拒絕發表他對他們指控的反駁[109]。後來的社會學家維爾納·科恩在對杭士基的立場進行批評的同時,發表了一篇題為《仇恨的夥伴:諾姆·杭士基與納粹大屠殺否認論者》的理性分析[110]。福里松事件對杭士基的職業生涯,尤其是在法國的職業生涯,產生了持久的、破壞性的影響[111][112]。
對宣傳和國際事務的批評:1980–2001年
編輯| 外部影片連結 | |
|---|---|
| 《製造共識:杭士基與媒體》,一部1992年的紀錄片,探討杭士基的同名作品及其影響 |
1985年,在美國支持康特拉對抗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尼加拉瓜革命中,杭士基親身前往馬拿瓜,會見工人組織和衝突中的難民,舉辦關於政治和語言學的公開講座[113]。這些講座中的許多內容被包含在了他1987年出版的書《關於權力與意識形態:馬拿瓜演講》中[114]。1983年,他出版了《致命三角》一書,並在書中認為美國不斷地利用以巴衝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15]。1988年,杭士基造訪了巴勒斯坦領土,目睹了以色列占領造成的影響[116]。
杭士基和赫爾曼於1988年出版的《製造共識︰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概述了他們理解中主流媒體的宣傳模式。他們認為,即使在沒有官方審查制度的國家,新聞仍被五種過濾機制進行審查,這些過濾機制極大地影響了新聞的內容和呈現方式[117]。這本書的靈感來自艾力克斯·凱里,並在隨後被改編為一部1992年的同名電影[118]。1989年,杭士基出版了《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一書。他在書中提出,一個穩健的民主制度需要公民對試圖控制他們的媒體和精英知識文化進行知識自衛[119]。到20世紀80年代,杭士基的一批學生已經成為傑出的語言學家,他們反過來開始擴展和修訂了杭士基的語言學理論[120]。
20世紀90年代的杭士基進一步接受了政治行動主義[121]。他繼續致力於東帝汶的獨立事業,在東帝汶救濟協會和東帝汶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的要求下,他於1995年訪問了澳大利亞,就這一問題發表演講[122]。他就這一問題所做的演講後成為了他1996年出版的《權力與期望》一書的一部分[122]。由於杭士基引起的國際宣傳,他的傳記作者沃夫岡·斯波里奇認為,杭士基在幫助東帝汶獨立事業上做的工作可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調查記者約翰·皮爾格[123]。1999年東帝汶從印度尼西亞獲得獨立後,澳大利亞領導的東帝汶國際部隊作為維和部隊抵達;杭士基對此仍持批評態度,他認為其目的是確保澳大利亞根據《帝汶缺口條約》獲得東帝汶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124]。
對伊拉克戰爭的批評及從麻省理工學院退休:2001–2017年
編輯2001年的九一一襲擊事件發生後,杭士基接受了大量的採訪;七故事出版社在當年10月整理並出版了這些採訪[125]。杭士基在這些採訪中認為,隨後的反恐戰爭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新發展,而是自至少從雷根時代以來政策和相應言論的延續[126]。2001年,他在新德里舉辦了D·T·拉克達瓦拉紀念講座[127]。2003年,他應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家協會的邀請訪問古巴[128];同年,杭士基出版了《霸權還是生存》一書,將美國的策略稱為「帝國大戰略」,並在書中對伊拉克戰爭及反恐戰爭的其他方面進行了批評[129]。這一時期,杭士基更經常地進行國際性演講[128]。
2002年,杭士基從麻省理工學院退休[130],但繼續以名譽教授的身份在校園裡進行研究並舉辦研討會[131]。同年,他訪問了土耳其,參加了一家因印刷杭士基的一本書而被指控犯叛國罪的出版商的審理;杭士基堅持要與該出版商一同作為被告出席,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下,安全法院在開庭第一天就撤銷了指控[132]。在該次旅行中,杭士基還去往了土耳其的庫爾德地區,並為庫德人的人權發聲[132]。作為世界社會論壇的支持者,他在2002年和2003年參加了在巴西舉行的會議和在印度舉行的論壇活動[133]。
杭士基支持占領運動,曾在占領運動人士的營地發表演講,並製作了兩部記錄其影響的作品:2012年出版的《占領》和2013年出版的小冊子《占領:對經典戰爭、叛亂和團結的反思》。他把占領運動的發展歸因於人們認為民主黨已經放棄了白人工人階級的利益[134]。2014年3月,杭士基以高級研究員的身份加入了支持廢除全球核武器的核時代和平基金會的諮詢委員會[135][136]。2015年的紀錄片《美國夢之安魂曲》通過「75分鐘的教學示威」總結了他對資本主義和貧富差距的看法[137]。
亞利桑那大學:2017年–
編輯2017年,杭士基在圖森的亞利桑那大學開了一門短學時的政治課程[138],後來又被聘為該校語言學系的兼職教授,其職責包括教學和舉行公開研討會[139]。他的工資由慈善機構的捐款支付[140]。
2018年,杭士基簽署了調和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波士尼亞克人和蒙特內哥羅人的《通用語言宣言》[141][142]。
2022年3月,喬姆斯基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稱為「重大戰爭罪」,與美國領導的入侵伊拉克和1939年德蘇入侵波蘭並列,並補充說:「去尋求解釋總是有意義的,但不應去為其辯解,也不應原諒」[143]。10月,杭士基呼籲美國「停止破壞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談判」[144]。
語言學理論
編輯杭士基的語言學理論的基礎為生物語言學,該語言學派認為,支撐語言結構的原理在生物學上被預設在了人類的大腦中,因此語言結構是遺傳性的[148]。杭士基認為,所有人類都有與社會文化差異無關的,相同的基本語言結構[149]。因此,杭士基反對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心理學,斯金納認為行為(包括說話和思考)完全是生物體與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學習產物。杭士基認為,語言是人類獨特的進化的結果,且與其他動物物種使用的交流模式不同[150][151]。杭士基的先天論、內在主義的語言觀與「理性主義」的哲學流派一致,同時與反先天論、外在主義、基於「經驗主義」哲學流派的語言觀相對[152],後者認為所有知識,包括語言,都來自於外界的環境[147]。
普遍文法
編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杭士基一直認為人類天生具有語言能力,並且生來就能理解語言中的文法,而這意味著兒童只需要學習其母語的某些特定的語言特徵便能掌握該種語言。他的論點基於對人類語言習得的觀察,並描述了「刺激貧乏」:在兒童所接觸的語言數目和他們所獲得的豐富語言能力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具體來說,儘管兒童只接觸到他們第一語言中有意義的句法變體中的一個非常小的有限子集,但他們卻以某種方式獲得了高度組織化和系統化的能力來理解和產生包括此前從未聽過的、無限多的句子[153]。為了解釋這一點,杭士基推斷,這一過程中所缺少的基本語言材料必須由先天的語言學能力補充。此外,儘管嬰兒和小貓都有歸納推理的能力,但即便他們接觸到完全相同的語言材料,人類總是會獲得理解和產生語言的能力,而小貓則永遠不會獲得這兩種能力。杭士基認為這種能力的差異是「語言習得裝置」所造成的,並認為語言學家需要確定該裝置具體是什麼,以及它可能對人類語言施加了什麼限制。杭士基認為這些限制產生的普遍特徵構成了「普遍文法」[154][155][156]。至今,已有多位學者對普遍文法理論提出了質疑,立論基礎包括語言的遺傳基礎在進化上是不可行的[157]、語言之間缺乏普遍特徵[158]以及先天/普遍結構和具體語言結構之間的聯繫未經證實[159]。學者麥可·托馬塞洛對杭士基的先天句法知識理論提出了質疑,同時認為該理論基於理性推導而非對具體行為進行觀察所得到的經驗[160]。儘管杭士基的內在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很有影響力,但由於其與研究證據不一致,最終該理論被主流兒童語言習得研究界所摒棄[161][162]。包括羅伯特·弗賴丁、傑佛瑞·桑普森、傑佛瑞·基思·普魯姆和芭芭拉·肖爾茨在內的語言學家也認為杭士基在這方面的語言學論據是錯誤的[163]。
轉換-生成文法
編輯轉換-生成文法是一種廣泛用於建模、編碼和推斷母語者的語言能力的理論[164]。其理論中的模型,或稱「形式文法」,表明某一語言的抽象結構可能與其他語言的具體結構有關[165]。杭士基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了轉換文法理論,其在之後的20年中一直是語言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句法理論[164]。「轉換」指的是語言內部的句法關係的轉換,例如,推斷出兩個句子的主語是同一個人[166]。杭士基的理論認為,語言由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組成。向外的表層結構將語音規則與聲音聯繫起來,而向內的深層結構則將單詞和概念意義聯繫起來。轉化-生成文法使用數學符號來描述意義和聲音(分別對應深層和表層結構)之間聯繫的規則。根據這一理論,語言學原理可以在數學上生成語言的潛在的句子結構[147]。
雖然今日人們普遍認為杭士基發明了轉換-生成文法,但在杭士基首次發表其理論時,他的理論並不被認為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杭士基在1955年的論文和1957年出版的書籍《句法結構》中介紹了由他的博士生導師澤里格·哈里斯和查爾斯·法蘭西斯·霍克特對他的理論的發展[f]。他們的方法源自丹麥結構語言學家路易·葉爾姆斯列夫的工作,葉爾姆斯列夫將算法文法引入了一般語言學[g]。杭士基基於這套符號串生成語言的理論,將邏輯上可能存在的文法分為四類,並將其合稱為杭士基譜系。這種分類方式下的四類文法呈現出層級關係,且較低級的文法包含較高級文法。這套理論今日仍在形式語言[167]和理論計算機科學領域,尤其是與程式語言理論相關的理論中被使用[168],如構建編譯器的有關理論和自動機理論中[169]。
轉換-生成文法理論及其衍生的管轄與約束理論是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早期學界進行研究時主要使用的框架,轉換-生成文法理論在今日學界轉向最簡方案理論後仍是一套重要的語言學理論[164]。最簡方案理論側重於語言學的原則與參數框架,這套框架假設人類語言有一組普遍的、不因語言和結構變化的文法原則,但其裝配有一組參數,而兒童學習的語言的過程是在具體的設定這些參數的值[170][171]。最簡方案理論同樣由杭士基提出[172],其主要探討哪套方案能夠以最優雅、最簡略、最自然的方式使用原則與參數框架[171]。為了將語言簡化成一個通過儘可能簡單的框架將聲音與意義連結起來的系統,杭士基拋棄了「深層結構」及「淺層結構」等概念,轉而強調腦神經的可塑性以及這種可塑性所帶來的無數的概念(邏輯形式)[151]。當接觸語言數據時,人的大腦會將聲音與意義相聯繫,而我們觀察到的文法規則實際上只是語言工作方式的後果和副產品。以此,杭士基將研究的重點從語言規則轉到了大腦用於產生這些規則及調節語言的機制上[151][173]。
政治立場
編輯杭士基是一位知名的政治異議人士[h]。他童年時曾受到猶太工人階級思想中政治行動主義影響[175],而自那之後他的政治立場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176]。他通常將自己描述為一位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或是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177]。他認為這些立場並不能代表精確的政治理論,只能代表他所認為人類需要達成的理想:自由意志、社群與結社自由[178]。與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其他一些社會主義者不同,杭士基認為政治不屬於科學[179],不過他仍讓他關於理想社會的想法植根於經驗數據和經驗結論之上[180]。
在杭士基看來,政治現實背後的真相受到精英企業集團系統性地扭曲和壓制,他們利用企業媒體、廣告和智庫來推動自己的宣傳工作。杭士基的著作試圖揭示這種操縱,以及他們所掩蓋的真相[181]。杭士基在著作中認為,這種弄虛作假的網絡可以通過「常識」、批判性思維以及了解自利和自欺的作用擊破[182],但知識分子們因為害怕失去名望和資金而放棄了講述世界真相的道德責任[183]。他還認為,作為一位特殊的知識分子,他有責任利用他的社會特權、資源和接受的訓練幫助民眾爭取民主[184]。
雖然杭士基參加過抗議遊行,組織過社運團體,但他的主要政治發聲渠道仍是通過教育和出版的方式。他寫了很多政治作品[185],作了許多免費講座和免費課程,並嘗試以這些舉措激起人們的政治意識[186]。他是世界產業工人的會員[187]。
批評反科學文化
編輯「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用我所知道的方法,那些被指責為「科學」、「理性」和「邏輯」的方法研究此類問題。因此當我讀那些論文(按:此處應指後現代或後結構的論文)時,我指望他們能幫我超越這種局限,或指出一個全新的方向。我恐怕是失望了。我承認這也許是我的局限性。通常我讀到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那些多音節術語的時候,只是匆匆掃過。我能理解的多半是老生常談或明顯的謬誤,然而那些只在所有詞語中占一小部分。確實,有很多其它東西我也不懂,比如最新的物理學和數學期刊上的文章。但是不一樣。後一種情況下,我知道如何去理解他們,在我格外感興趣的時候也那樣做過;而且我知道那些領域的人能夠根據我的水平向我解釋,讓我弄懂我感興趣的部分內容。相反,好像沒有人能跟我解釋最新的「後」什麼之類的理論。除了老生常談,胡言亂語和明顯的錯誤外還有些什麼,我也就不知道如何進一步去理解。」
杭士基注意到,對「白人男性科學」的批判類似於反猶主義及「德意志物理學」運動期間,納粹出於詆毀猶太科學家的研究的政治目的對「猶太物理學」的攻擊。
「事實上,「白人男性科學」的整套說法都讓我想起「猶太物理學」。也許這是我的另一個不足之處,但是我讀一篇科學論文的時候無法判斷作者是否白人或者男性。對課堂上、辦公室或其它地方的討論也是如此。我著實懷疑那些與我共事的非男性、非白人學生、朋友和同事會樂於接受這種說法,承認他們的思維和理解方式由於「性別與種族的文化」而與「白人男性科學」有所不同。我估計他們對此的反應不僅僅是「驚訝」。」
政治
編輯杭士基對美國政府一貫持鮮明的批判立場,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成為他的很多政論的基點之一。杭士基對此提出兩點理由:首先,他相信,如果他的著作是針對自己國家的政府,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其次,他認為,美國作為世界上現存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以前的所有超級大國一樣霸道。他對美國外交政策及美國權力合法性的批判影響深遠,並因而成為富有爭議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誠追隨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來越多的批評,尤其是針對他對911事件的反應。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給杭士基帶來了人身威脅。他的名字被列在泰德·卡辛斯基(「郵箱炸彈殺手」)的預定名單上。在卡辛斯基被捕以前,杭士基讓人檢查收到的郵件以防炸彈。他自稱也經常被警察保護,特別是在麻省理工校園的時候,雖然他原則上不同意這種保護[188]。
杭士基說,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小布希和歐巴馬等人被逮捕並移送國際刑事法庭,但他知道這不可能實現,因為:美國通過一項法律,授權總統派軍行使武力救回任何被移送國際刑事法庭的美國人。
儘管對美國百般批評,杭士基還是生活在美國,他的解釋是: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189]。後來他又闡發為:「國與國之間的綜合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會這麼比較。不過美國有些成就,特別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190]
2013年,土耳其抗議運動支持者,至麻省理工邀請杭士基聲援。杭士基同樣舉起I'm also a çapulcu,聲援土耳其反對派。2018年,杭士基與約翰·羅莫等30多名左派學者共同呼籲抵制中國舉辦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杭士基發表聲明稱世界各地的左派學者都應該加入抵制此類大會和活動的行列;而羅莫則發表聲明稱,相關行為暴露出中國政治領導層是假馬克思主義者[191]。
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議裏爆發了香港中文大學衝突,香港警察攻進了香港的知名學府中文大學,諾姆·杭士基參與了香港監察發起的學術界聯署,譴責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192],並促請香港政府"捍衛學術自由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它參與的學者包括齊澤克、朱迪斯·巴特勒、揚尼斯·瓦魯法基斯、羅伯特·彼得·喬治和史迪芬·平克。
論恐怖主義
編輯針對美國在1981年和2001年宣布的反恐戰爭,杭士基認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源頭是美國領導的世界強國。他引用一部美國軍事辭典中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說那是:「故意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以策動恐懼,試圖強迫或恐嚇政府或社會以追求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標。」他據此指出,恐怖主義是對某種行為的客觀描述,不論行動者是否為國家機器。就美國入侵阿富汗,他說:「肆意殺害無辜平民是恐怖主義而非反恐戰爭。」論恐怖主義的效力:「首先,恐怖主義確實有效,不會失敗。它是有效的。暴力總是有效,世界歷史一向如此。其次,通常所謂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這一說法是極大的分析失誤。與其他暴力手段一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強者的武器。恐怖主義被稱作弱者的武器,是因為:強者同時控制著言論,他們的恐怖行徑也就可以不算。這是普遍情況。我幾乎想不出歷史上有任何反例,甚至十惡不赦的劊子手也這麼看。比如說納粹,他們沒有在歐洲占領地實行恐怖主義,他們是保護當地居民免受游擊隊的恐怖襲擊。正如其它抵抗運動一樣,當中存在恐怖主義。納粹是在反恐怖。」[193]
至於對恐怖主義是應當譴責還是支持,杭士基認為,恐怖主義(及暴力和強權)總的來說應受譴責,除非在某些情況下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恐怖(或暴力及濫用強權)。在1967年一場關於政治暴力的合法性的辯論中,杭士基主張,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活動是不正當的,但是從理論上來講,在某些情況下那些活動又是有理由的:
「我不認為由於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活動令人髮指,就應該對之一味譴責。雖然這可能聽上去很邪惡,但我們實在應當把代價作個比較。如果我們要站在道德立場上看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應當如此—我們就要問一問:使用和不使用恐怖活動的結果分別是什麼。如果不使用恐怖活動的後果就是讓越南的農民繼續過著菲律賓農民那樣的生活,那我想恐怖活動是有合法性的。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說,我不認為成功是通過恐怖活動取得的。」[194]
杭士基認為,那些美國政府進行的被他稱為恐怖主義的活動都禁不住這樣的檢驗。對美國政策的譴責是他的著作的要點之一。
2013年9月,杭士基接受今日俄羅斯訪問,以曼德拉和海珊為例說明,美國的「恐怖份子清單」是根據政治需要來決定誰該列入或移出,是不受監督的作法。杭士基說:「歐巴馬寧可錯殺一百的『全球暗殺政策』(global assassination campaign),倒退到8百年前13世紀的人權水平。」[195]
其他學術貢獻
編輯杭士基的語言學著作,對於心理學在20世紀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普遍文法理論被很多人認為是對既定的行為主義理論的直接挑戰。這一理論對於理解兒童如何習得語言以及什麼是真正理解語言的能力都有深遠的意義。杭士基理論的很多基本原則現在已經在某些圈子裡被普遍接受。1959年杭士基出版了對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的《口語行為》一書的長篇評論。斯金納在他的書裡試圖用行為學理論解釋語言問題,他將「口語行為」定義為一種從他人那裡學習得來的行為,這就超出了語言學家通常關注的範圍而對交往行為提出了普遍解釋。
斯金納的研究方式與傳統語言學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於它關注語言使用的情境,比如他認為跟人要水,與把一樣東西稱為水,與回應他人要水的請求在功能上是不同的。這種因功能而異的回應方式需要單獨進行解釋,這就與傳統的語言觀以及杭士基的心理語言學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關注的是詞語的精神表象,並假定某個詞一旦被學會就會以各種功能出現。杭士基1959年對斯金納的批判雖然也涉及不同口頭行為的功能,但主要集中在對斯金納理論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行為心理學的批判。杭士基論文的主要觀點是,將動物研究中的行為原則應用到實驗室之外的人類身上是毫無意義的, 要想理解人類的複雜行為,我們必須假定負有終極責任的大腦中有一些無法被觀測到的實體。這兩點都與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針鋒相對。應該注意到,杭士基1959年的這篇論文也曾受到嚴厲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肯尼斯·麥克考科戴爾1970年發表在《行為的實驗性分析期刊》(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volume 13, pages 83-99)上的《論杭士基對斯金納〈口語行為〉的評論》。這篇論文和其它類似的評論都指出一些為外行忽略的事實:比如杭士基不管是對行為心理學還是對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都並不真正了解,而且犯了很多令人難堪的錯誤。正因為如此,杭士基的論文並未完成它所宣稱的任務。那些深受這篇論文影響的人,要麼是從來就與他觀點一致,要麼從來沒讀過這篇文章。
通常認為杭士基對斯金納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設的批評開創了美國心理學從1950年代到70年代的「認知革命」,也就是從以行為研究為主轉變為認知研究為主。杭士基在他1966年的《笛卡爾主義語言學》和後來的著作中對人類語言能力作出的解釋後來成為心理學某些領域的研究範本。現在很多關於頭腦如何運作的觀念都是從杭士基富有說服力的思想中發展而來的。有三個基本思想。首先,頭腦是「認知的」,或者說頭腦中包含精神狀況、看法、疑惑等等。先前的觀念甚至不承認這一點,認為只存在「如果你問我想不想要X,我會回答是的」這樣的邏輯關係。而杭士基則相信通常的看法一定是正確的,即頭腦中包含看法甚至無意識的精神狀態。其次,杭士基認為成年人的大部分智力活動都是「先天的」。儘管兒童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說某種語言,所有兒童都天生具有很強的「語言學習」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得以在最初幾年中很快吸收幾種語言。後來的心理學家將這一論斷廣泛應用於語言問題之外。最後,杭士基將「模塊化」作為頭腦認知結構的關鍵特徵。他認為頭腦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各司其職的亞系統組成的,彼此間進行有限的交流。
杭士基在開始認為語言不是適應器,而是人腦急速增長的副產物[196],即只要把幾十億個神經元放在一起封裝在頭骨這個狹小空間內,語言就會自然出現,而竝非特意設計出來解決適應性問題的;不過近年來杭士基的觀點開始變得模稜兩可,開始認為語言也可能源自遠古人類面臨的獨特的選擇壓力,可能是進化而來的適應器[197]。
杭士基的模式也被當做其他一些領域的理論基礎。計算機科學的基礎課程中會涉及杭士基體系,因為它傳達了對多種正規語言的洞見。這一體系也可以從數學的角度來討論,並引起了數學家,尤其是組合數學家的興趣。很多演化心理學的論點也是由杭士基的研究結果中引發的。
1984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喬治斯·克勒,色薩·米爾斯坦,和尼爾斯·吉爾內用杭士基的生成模式解釋人類免疫系統,他把「蛋白質結構的各種特徵」類比為「生成文法的各個組成部分」。吉爾內的斯德哥爾摩諾貝爾講座就題名為「免疫系統的生成文法」。杭士基的生成文法理論也影響了音樂理論和分析的工作。
參見
編輯注釋
編輯- ^ 其中之一為阿維瓦·杭士基
- ^ 英語音標: i/noʊm ˈtʃɒmski/,NOHM CHOM-skee;希伯來語音標:[ˈnoʔam ˈχomski]。中國大陸多譯作艾弗拉姆·諾姆·喬姆斯基。
- ^ "In thinking about the Effect of Chomsky's work, we have had to dwell upon the reception of Chomsky's 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Chomsky as a Jew, a linguist, a philosopher, a historian, a gadfly, an icon, and an anarchist. [在思考杭士基作品的效果時,我們不得不糾結於杭士基作品的接受程度,以及人們對於杭士基猶太人、語言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討厭鬼、偶像及無政府主義者身份的看法。]" (Barsky 2007,第107頁)
- ^ "Since his Cartesian linguistics (1966) it has been clear that Chomsky is a superb intellectual historian—a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in the case of his 1966 book, his earliest incursion into the field; later writings (e.g., Year 501) extended the coverage to world history. The lectures just mentioned and other writings take on highly significant and sometimes not properly appreciated, and often misunderstood,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很明顯,自他出版了《笛卡爾語言學》以來,杭士基就成為了一位出色的知識分子、史學家——就他1966年的書而言,還僅是一位哲學史學家,這也是他對史學界最早的涉獵;後來的著作(如《501年》)將覆蓋面擴大到世界歷史。剛剛提到的講座和其他著作對科學史上高度重要的、有時沒有得到正確理解的、經常被誤解的發展進行了研究。]" (Otero 2003,第416頁)
- ^
- Fox 1998: "Mr. Chomsky ... is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and remains the field's most influential practitioner. [杭士基先生[……]是現代語言學之父,今日仍然是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實踐者。]"
- Tymoczko & Henle 2004,第101頁: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Noam Chomsky, observed, each of the following sequences of words is nonsense ... [正如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諾姆·杭士基所觀察到的,以下每一個詞序列都是沒有意義的……]"
- Tanenhaus 2016: "At 87, Noam Chomsky, the found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remains a vital presence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87歲的諾姆·杭士基,今日仍然是美國知識界的一個重要存在。]"
- ^
- Smith 2004,第107頁 "Chomsky's early work was renowned for its mathematical rigor and he mad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nascent discipline of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in particular the analysis of (formal) languages in terms of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Chomsky hierarchy. [杭士基的早期著作就以數學的縝密性著稱,尤其是用「杭士基層級」對(形式)語言所做的分析]"
- Koerner 1983,第159頁: "Characteristically, Harris proposes a transfer of sentences from English to Modern Hebrew [...] Chomsky's approach to syntax in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several years thereafter wa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Harris's approach, since the concept of 'deep' or 'underlying structure' had not yet been introduced.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Harris (1954) and Chomsky (1957) appears to be that the latter is dealing with transfers within one single language only [十分特色的一點在於,哈里斯提出了從英語到現代希伯來語的句子轉換[……]杭士基在《句法結構》中以及此後幾年對句法的研究方法與哈里斯的方法沒有什麼不同,因為當時還沒有引入「深層」或「基本結構」的概念。哈里斯(1954)和杭士基(1957)兩人的研究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後者只處理了一種單一語言內的轉換問題]"
- ^
- Koerner 1978,第41f頁: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Chomsky cites Hjelmslev's Prolegomena, which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953, since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argument, derived largely from logic and mathematics, exhibits noticeable similarities. [值得注意的是,杭士基引用了葉爾姆斯列夫於1953年被翻譯成英文的《語言理論導論》,因為該書作者的理論論證方式主要基於邏輯和數學,這與杭士基的理論論證方式表現出明顯的相似性。]"
- Seuren 1998,第166頁: "Both Hjelmslev and Harris were inspired by the mathematical notion of an algorithm as a purely formal production system for a set of strings of symbols. [...] it is probably accurate to say that Hjelmslev was the first to try and apply it to the generation of strings of symbols in natural language. [葉爾姆斯列夫和杭士基都受到了算法是一組符號串的純形式產生系統這一數學概念的啟發[……]也許可以準確地說,葉爾姆斯列夫是第一個嘗試將其應用於自然語言中的符號串的生成的人。]"
- Hjelmslev 1969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Danish original 1943;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1954.
- ^
- Macintyre 2010
- Burris 2013: "Noam Chomsky has built his entire reputation as a political dissident on his command of the facts. [諾姆·杭士基將他作為政治異見者的全部聲譽建立於他對事實的掌握之上。]"
- McNeill 2014: "[Chomsky is] often dubbe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intellectuals and its leading public dissident... [[乔姆斯基]常被稱為世界上最重要知識分子之一,也是一位重要的公開持不同政見者。]"
參考文獻
編輯引用
編輯- ^ Partee 2015,第328頁.
- ^ 2.0 2.1 Chomsky 1991,第50頁.
- ^ Sperlich 2006,第44–45頁.
- ^ Slife 1993,第115頁.
- ^ Barsky 1997,第58頁.
- ^ Antony & Hornstein 2003,第295頁.
- ^ Chomsky 2016.
- ^ Harbord 1994,第487頁.
- ^ 9.0 9.1 9.2 9.3 9.4 Barsky 2007,第107頁.
- ^ Smith 2004,第185頁.
- ^ MIT Tech Talk 1992.
- ^ Lyons 1978,第xv頁; Barsky 1997,第9頁; McGilvray 2014,第3頁.
- ^ 13.0 13.1 Barsky 1997,第9–10頁; Sperlich 2006,第11頁.
- ^ Barsky 1997,第9頁.
- ^ 荊其誠; 傅小蘭 (編). 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三) 1.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2021-09-12]. ISBN 978-7-301-19518-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12) (中文).
- ^ Barsky 1997,第11頁.
- ^ Feinberg 1999,第3頁.
- ^ 18.0 18.1 Barsky 1997,第11–13頁; Sperlich 2006,第11頁.
- ^ Barsky 1997,第11–13頁.
- ^ Barsky 1997,第15頁.
- ^ Lyons 1978,第xv頁; Barsky 1997,第15–17頁; Sperlich 2006,第12頁; McGilvray 2014,第3頁.
- ^ Lyons 1978,第xv頁; Barsky 1997,第21–22頁; Sperlich 2006,第14頁; McGilvray 2014,第4頁.
- ^ 23.0 23.1 Lyons 1978,第xv頁; Barsky 1997,第15–17頁.
- ^ Barsky 1997,第14頁; Sperlich 2006,第11, 14–15頁.
- ^ Barsky 1997,第23頁.
- ^ Lyons 1978,第xv頁; Barsky 1997,第15–17頁; Sperlich 2006,第13頁; McGilvray 2014,第3頁.
- ^ Barsky 1997,第17–19頁.
- ^ Barsky 1997,第17–19頁; Sperlich 2006,第16, 18頁.
- ^ Barsky 1997,第47頁; Sperlich 2006,第16頁.
- ^ Barsky 1997,第47頁.
- ^ Sperlich 2006,第17頁.
- ^ Barsky 1997,第48–51頁; Sperlich 2006,第18–19, 31頁.
- ^ Barsky 1997,第51–52頁; Sperlich 2006,第32頁.
- ^ Barsky 1997,第51–52頁; Sperlich 2006,第33頁.
- ^ Sperlich 2006,第33頁.
- ^ Lyons 1978,第xv頁; Barsky 1997,第79頁; Sperlich 2006,第20頁.
- ^ 37.0 37.1 Sperlich 2006,第34頁.
- ^ Sperlich 2006,第33–34頁.
- ^ Barsky 1997,第81頁.
- ^ Barsky 1997,第83–85頁; Sperlich 2006,第36頁; McGilvray 2014,第4–5頁.
- ^ Sperlich 2006,第38頁.
- ^ Sperlich 2006,第36頁.
- ^ Barsky 1997,第13, 48, 51–52頁; Sperlich 2006,第18–19頁.
- ^ Sperlich 2006,第20頁.
- ^ Sperlich 2006,第20–21頁.
- ^ Barsky 1997,第82頁; Sperlich 2006,第20–21頁.
- ^ Barsky 1997,第24頁; Sperlich 2006,第13頁.
- ^ Barsky 1997,第24–25頁.
- ^ Barsky 1997,第26頁.
- ^ Barsky 1997,第34–35頁.
- ^ Barsky 1997,第36頁.
- ^ Chomsky and the Marlenites. [2010-04-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6-29).
- ^ Personal influences, by Noam Chomsky (Excerpted from The Chomsky Reader). Chomsky.info. [2018-0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8).
- ^ Lyons 1978,第xv頁; Barsky 1997,第86–87頁; Sperlich 2006,第38–40頁.
- ^ Barsky 1997,第87頁.
- ^ Lyons 1978,第xvi頁; Barsky 1997,第91頁.
- ^ Barsky 1997,第91頁; Sperlich 2006,第22頁.
- ^ Barsky 1997,第88–91頁; Sperlich 2006,第40頁; McGilvray 2014,第5頁.
- ^ Barsky 1997,第88–91頁.
- ^ Lyons 1978,第1頁.
- ^ Lyons 1978,第xvi頁; Barsky 1997,第84頁.
- ^ Lyons 1978,第6頁; Barsky 1997,第96–99頁; Sperlich 2006,第41頁; McGilvray 2014,第5頁.
- ^ MacCorquodale 1970,第83–99頁.
- ^ Barsky 1997,第119頁.
- ^ Barsky 1997,第101–102, 119頁; Sperlich 2006,第23頁.
- ^ Barsky 1997,第102頁.
- ^ Knight 2018.
- ^ Barsky 1997,第103頁.
- ^ Barsky 1997,第104頁.
- ^ Lyons 1978,第xvi頁; Barsky 1997,第120頁.
- ^ Barsky 1997,第122頁.
- ^ Sperlich 2006,第60–61頁.
- ^ Barsky 1997,第114頁.
- ^ Sperlich 2006,第78頁.
-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6-06-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4-08).
- ^ Barsky 1997,第120, 122頁; Sperlich 2006,第83頁.
- ^ Lyons 1978,第xvii頁; Barsky 1997,第123頁; Sperlich 2006,第83頁.
- ^ Chomsky, Noam. At war with Asia 1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ISBN 9780394462103.
- ^ Lyons 1978,第xvi–xvii頁; Barsky 1997,第163頁; Sperlich 2006,第87頁.
- ^ Lyons 1978,第5頁; Barsky 1997,第123頁.
- ^ Barsky 1997,第134–135頁.
- ^ Barsky 1997,第162–163頁.
- ^ Lyons 1978,第5頁; Barsky 1997,第127–129頁.
- ^ Lyons 1978,第5頁; Barsky 1997,第127–129頁; Sperlich 2006,第80–81頁.
- ^ Barsky 1997,第121–122, 131頁.
- ^ Barsky 1997,第121頁; Sperlich 2006,第78頁.
- ^ Barsky 1997,第121–122, 140-141頁; Albert 2006,第98頁; Knight 2016,第34頁.
- ^ Barsky 1997,第153頁; Sperlich 2006,第24–25, 84–85頁.
- ^ Barsky 1997,第124頁; Sperlich 2006,第80頁.
- ^ Barsky 1997,第123–124頁; Sperlich 2006,第22頁.
- ^ 91.0 91.1 Barsky 1997,第143頁.
- ^ Lyons 1978,第xv–xvi頁; Barsky 1997,第120, 143頁.
- ^ 93.0 93.1 Barsky 1997,第156頁.
- ^ Greif 2015,第312–313頁.
- ^ 95.0 95.1 Sperlich 2006,第51頁.
- ^ Barsky 1997,第175頁.
- ^ Barsky 1997,第167, 170頁.
- ^ Barsky 1997,第157頁.
- ^ Barsky 1997,第160–162頁; Sperlich 2006,第86頁.
- ^ Sperlich 2006,第85頁.
- ^ Barsky 1997,第187頁; Sperlich 2006,第86頁.
- ^ Barsky 1997,第187頁.
- ^ Sperlich 2006,第103頁.
- ^ Lukes 1980.
- ^ Barsky 1997,第187–189頁.
- ^ 106.0 106.1 Barsky 1997,第190頁.
- ^ Barsky 1997,第179–180頁; Sperlich 2006,第61頁.
- ^ Barsky 1997,第185頁; Sperlich 2006,第61頁.
- ^ Barsky 1997,第184頁.
- ^ Barsky 1997,第78頁.
- ^ Barsky 1997,第185頁.
- ^ Birnbaum 2010; Aeschimann 2010.
- ^ Sperlich 2006,第91, 92頁.
- ^ Sperlich 2006,第91頁.
- ^ Sperlich 2006,第99頁; McGilvray 2014,第13頁.
- ^ Sperlich 2006,第98頁.
- ^ Barsky 1997,第160, 202頁; Sperlich 2006,第127–134頁.
- ^ Sperlich 2006,第136頁.
- ^ Sperlich 2006,第138–139頁.
- ^ Sperlich 2006,第53頁.
- ^ Barsky 1997,第214頁.
- ^ 122.0 122.1 Sperlich 2006,第104頁.
- ^ Sperlich 2006,第107頁.
- ^ Sperlich 2006,第109–110頁.
- ^ Sperlich 2006,第110–111頁.
- ^ Sperlich 2006,第143頁.
- ^ The Hindu 2001.
- ^ 128.0 128.1 Sperlich 2006,第120頁.
- ^ Sperlich 2006,第114–118頁.
- ^ Weidenfeld 2017.
- ^ Sperlich 2006,第10頁.
- ^ 132.0 132.1 Sperlich 2006,第25頁.
- ^ Sperlich 2006,第112–113, 120頁.
- ^ Younge & Hogue 2012.
- ^ NAPF 2014.
- ^ Ferguson.
- ^ Gold 2016.
- ^ Harwood 2016.
- ^ Ortiz 2017.
- ^ Mace.
- ^ Vučić 2018.
- ^ Bobanović 2018.
- ^ Noam Chomsky: US Military Escalation Against Russia Would Have No Victors. Truthout. 2022-03-01 [2022-12-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04).
- ^ Noam Chomsky & Vijay Prashad: U.S. Must Stop Undermining Negotiations with Russia to End Ukraine War. Democracy Now!. [2022-11-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1-27) (英語).
- ^ 喬姆斯基在巴西治療,半身不遂每天看報. 新浪香港. 2024-06-12 [2024-06-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6-20).
- ^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健康状况恶化,据称“目前已无法交流”. 新京報. 2024-06-11 [2024-06-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6-20).
- ^ 147.0 147.1 147.2 Baughman et al. 2006.
- ^ Lyons 1978,第4頁; McGilvray 2014,第2–3頁.
- ^ Lyons 1978,第7頁.
- ^ Lyons 1978,第6頁; McGilvray 2014,第2–3頁.
- ^ 151.0 151.1 151.2 Brain From Top To Bottom.
- ^ McGilvray 2014,第11頁.
- ^ Dovey 2015.
- ^ Chomsky.
- ^ Thornbury 2006,第234頁.
- ^ O'Grady 2015.
- ^ Christiansen & Chater 2010,第489頁; Ruiter & Levinson 2010,第518頁.
- ^ Evans & Levinson 2009,第429頁; Tomasello 2009,第470頁.
- ^ Tomasello 2003,第284頁.
- ^ Tomasello 1995,第131頁.
- ^ Fernald & Marchman 2006,第1027–1071頁.
- ^ de Bot 2015,第57–61頁.
- ^ Pullum & Scholz 2002,第9—50頁.
- ^ 164.0 164.1 164.2 Harlow 2010,第752頁.
- ^ Harlow 2010,第752–753頁.
- ^ Harlow 2010,第753頁.
- ^ Butterfield, Ngondi & Kerr 2016.
- ^ Knuth 2002.
- ^ Davis, Weyuker & Sigal 1994,第327頁.
- ^ 程工. Chomsky最简方案形成的理论动因. 外語教學與研究. 1998, (1) [2022-0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31).
- ^ 171.0 171.1 Hornstein 2003.
- ^ Szabó 2010.
- ^ Fox 1998.
- ^ McGilvray 2014,第12頁.
- ^ Sperlich 2006,第77頁.
- ^ Barsky 1997,第95頁; McGilvray 2014,第4頁.
- ^ Sperlich 2006,第14頁; McGilvray 2014,第17, 158頁.
- ^ McGilvray 2014,第17頁.
- ^ Sperlich 2006,第74頁; McGilvray 2014,第16頁.
- ^ McGilvray 2014,第222頁.
- ^ Sperlich 2006,第8頁; McGilvray 2014,第158頁.
- ^ Sperlich 2006,第74頁; McGilvray 2014,第12–13頁.
- ^ McGilvray 2014,第159頁.
- ^ McGilvray 2014,第161頁.
- ^ McGilvray 2014,第158頁.
- ^ Sperlich 2006,第71頁.
- ^ IWoW biographies.
- ^ "The Cutting Edge of the Political Lef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arch 13, 2006 The Hour CBC
- ^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Bill Bennet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ay 30, 2002 American Morning with Paula Zahn CNN
- ^ "Question tim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November 30, 2003 The Observer
- ^ 楊緣. 乔姆斯基等学者呼吁抵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会. 金融時報. 2018-11-28 [2018-1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1-28).
- ^ 逾 3,700 國際知名學者聯署 譴責香港警暴 促大學拒警進入校園.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2020-02-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19) (英語).
- ^ Noam Chomsky. The New War Against Terror. chomsky.info // Delivered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ctober 18, 2001 [2013-09-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1).
- ^ The Legitimacy of Violence as a Political Ac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Noam Chomsky debates with Hannah Arendt, Susan Sontag, et al.
- ^ 台灣立報 2013-02-08 :海珊與曼德拉. [2013-12-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2-10).
- ^ Chomsky, 1991
- ^ Hauser, Chomsky, &Fitch, 2002
來源
編輯- Adams, Tim. Noam Chomsky: Thorn in America's side. The Guardian. 2003-11-30 [2016-05-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5-16).
- Aeschimann, Eric. Chomsky s'est exposé, il est donc une cible désignée. Libération. 2010-05-31 [2010-06-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9-26) (法語).
Chomsky a été violemment blessé du fait qu'une parti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aient pu le croire en accord avec Faurisson, en contradiction avec tous ses engagements et toute sa vie.
- Albert, Michael. Remembering Tomorrow: From the politics of opposition to what we are for. Seven Stories Press. 2006: 97–99. ISBN 978-158322742-8.
- Antony, Louise M.; Hornstein, Norbert (編). Chomsky and His Cri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295. ISBN 978-0-631-20021-5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to speak to Litndeb. 2009-01-09 [2016-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5-11).
- Author, activist Noam Chomsky to receive awar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10-03-29 [2016-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12-09).
- Baroni, M.; Callegari, L. (編). Musical grammars and computer analysis.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1982: 201–218. ISBN 978-882223229-8.
- Barsky, Robert F. Noam Chomsky: A Life of Diss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ISBN 978-0-262-02418-1.
- Barsky, Robert F. The Chomsky Effect: A Radical Works Beyond the Ivory Tower. MIT Press. 2007: 107. ISBN 978-026202624-6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Baughman, Judith S.; Bondi, Victor; Layman, Richard; McConnell, Tandy; Tompkins, Vincent (編). Noam Chomsky. American Decades. Detroit, MI: Gale. 2006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14).
- Birnbaum, Jean. Chomsky à Paris: chronique d'un malentendu. Le Monde des Livres. Le Monde. 2010-06-03 [2010-06-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7) (法語).
Le pays de Descartes ignore largement ce rationaliste, la patrie des Lumières se dérobe à ce militant de l'émancipation. Il le sait, et c'est pourquoi il n'y avait pas mis les pieds depuis un quart de siècle.
- Bobanović, Paula. Chomsky: Hrvati, Srbi i Bošnjaci govore isti jezik [杭士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波士尼亞人說的是同一種語言]. Express.hr (Zagreb). 2018-04-14 [2018-07-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07)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 Boden, Margaret A. Mind As Machine: a His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19924144-6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de Bot, Kees. A Histo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1980 to the Present. Routledge. 2015. ISBN 978-113882065-4.
- Braun, Stuart. Dissident intellectual Noam Chomsky at 90. Deutsche Welle. 2018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05).
- British Academy announces 2014 prize and medal winners. British Academy. 2014-07-24 [2017-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0-19).
- Bronner, Ethan. Israel Roiled After Chomsky Barred From West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2010-05-17 [2016-05-04].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4).
- Burris, Greg. What the Chomsky-Žižek debate tells us about Snowden's NSA revelations. The Guardian. 2013-08-11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16).
- Butterfield, Andrew; Ngondi, Gerard Ekembe; Kerr, Anne (編). Chomsky hierarchy. A Dictionary of Computer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21-08-13]. ISBN 978-0-19-968897-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8).
- Campbell, Duncan. Chomsky is voted world's top public intellectual. The Guardian. 2005-10-18 [2021-08-13]. ISSN 0261-307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6-15).
- Chomsky. inventio-musikverlag.de. [201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8-05).
- Chomsky Amid the Philosopher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2014-01-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13).
- Chomsky Is Citation Champ. MIT Tech Talk 36 (27). 1992-04-15 [2019-09-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3) –透過MIT News.
- Chomsky is Citation Champ. MIT. 1992-04-15 [2007-09-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3).
- Chomsky, Noam. The 'Chomskyan Era' (excerpted from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Chomsky.info. [2017-0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23).
- Chomsky, Noam. Kasher, Asa , 編.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 Problems and Mysteries. Oxford: Blackwell. 1991: 50.
- Chomsky, Noam. Class Warfare: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Pluto Press. 1996: 135–136. ISBN 978-074531137-1.
- Chomsky, Noam. Is the US Ready for Socialism? A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Truthout. C.J. Polychroniou. 2016-05-18 [2019-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7). also available, in part, on chomsky.info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Chomsky: Saudi Arabia is the "Center of Radical Islamic Extremism" Now Spreading Among Sunni Muslims. Democracy Now!. 2016-05-17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5).
- Christiansen, Morten H.; Chater, Nick. Language as shaped by the br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October 2010, 31 (5): 489–509. ISSN 1469-1825. PMID 18826669. doi:10.1017/S0140525X08004998.
- Cipriani, Enrico. Some reflections on Chomsky's notion of reference. Linguistics Beyond and within. 2016, 2: 44–60. doi:10.31743/lingbaw.5637 .
- Cohn, Werner. Partners in Hate: Noam Chomsky and the Holocaust Deniers. Cambridge, MA: Avukah Press. 1995 [First published 1985]. ISBN 978-0-9645897-0-4.
- Cowley, Jason. New Statesman – Heroes of our time – the top 50. New Statesman. 2006-05-22 [2015-12-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12-27).
- Davis, Martin; Weyuker, Elaine J.; Sigal, Ron. Computability, complexity, and languages: fundamentals of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2nd. Boston: Academic Press, Harcourt, Brace. 1994: 327. ISBN 978-0-12-206382-4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Denied Entry: Israel Blocks Noam Chomsky from Entering West Bank to Deliver Speech. Democracy Now!. 2010-05-17 [2016-05-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7).
- Dovey, Dana. Noam Chomsky's Theory Of Universal Grammar Is Right; It's Hardwired Into Our Brains. Medical Daily. 2015-12-07 [2017-08-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12).
- The Erdös Number Project. Oakland University. 2017-11-21 [2017-12-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0-22).
- Erich-Fromm-Preis: Noam Chomsky in Stuttgart geehrt. Stuttgarter Zeitung. Deutsche Presse-Agentur. 2010-03-23 [2019-08-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6) (德語).
- Evans, Nicholas; Levinson, Stephen C. The myth of language universals: Language d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gnitive sci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October 2009, 32 (5): 429–448. ISSN 1469-1825. PMID 19857320. doi:10.1017/S0140525X0999094X .
- Feinberg, Harriet. Elsie Chomsky: A Life in Jewish Education (PDF). Cambridge, Mass.: Brandeis University. 1999-02 [2019-01-10].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08-05-11).
- Ferguson, Joe. Tickets on sale for Tucson talk on nuclear war with Noam Chomsky, Daniel Ellsberg. Arizona Daily Star. [2018-07-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4).
- Fernald, Anne; Marchman, Virginia A. Language learning in infancy. Traxler, Matthew; Gernsbacher, Morton Ann (編).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Academic Press. 2006: 1027–1071. ISBN 978-008046641-5.
- Flint, Anthony. Divided Legacy. The Boston Globe. 1995-11-19: 25. ISSN 0743-1791. ProQuest 290754647.
- Flood, Alison. As Hay festival opens in the UAE, authors condemn free speech abuses. The Guardian. 2020-02-24 [2020-02-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7).
- Fox, Margalit. A Changed Noam Chomsky Simplifies. The New York Times. 1998-12-05 [2016-02-22].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7).
- Friesen, Norm. The Textbook and the Lectur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New Med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7-12-10. ISBN 978-142142434-7.
- Fulton, Scott M., III. John W. Backus (1924–2007). BetaNews. 2007-03-20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4-22).
- Gendzier, Irene. 15: Noam Chomsky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Israel: Bearing Witness. McGilvray, James (編).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omsky 2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14–329. ISBN 978-131673875-7.
- Glaser, John. It is not a war. It is murder. antiwar.com. 2012-11-18 [2019-06-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08).
- Gold, Daniel M. Review: Noam Chomsky Focuses on Financial Inequality in 'Requiem for the American Dream'. The New York Times. 2016-01-28 [2016-06-01].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7).
- Gould, S. J. Official Transcript for Gould's deposition in McLean v. Arkansas. 1981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2-18).
- Graham, George. Behaviorism. Zalta, Edward N. (編).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9.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9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9).
- Greif, Mark. The Age of the Crisis of Man: Thought and Fiction in America, 1933–197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ISBN 978-0-691-14639-3.
- Hamans, Camiel; Seuren, Pieter A. M. Chomsky in search of a pedigree. Kibbee, Douglas A. (編). Chomskyan (R)evolutions. John Benjamins. 2010: 377–394 [2021-08-13]. ISBN 978-902721169-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8).
- Harbord, Shaun. Extracts form 'An historian's appraisal of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Noam Chomsky'. Otero, Carlos Peregrín (編). Noam Chomsky: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s 2–3. Taylor & Francis. 1994: 487 [2021-08-13]. ISBN 978-0-415-10694-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6).
- Harlow, S. J.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Evolution. Barber, Alex; Stainton, Robert J. (編).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lsevier: 752–770. 2010. ISBN 978-0-08-096501-7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Harris, R. Allen. Chomsky's other Revolution. Kibbee, Douglas A. (編). Chomskyan (R)evolution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237–265. ISBN 978-90-272-1169-9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Harwood, Lori. Noam Chomsky to Teach Politics Course In Spring. UA News. 2016-11-21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3).
- Hjelmslev, Louis.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First published 1943]. ISBN 029902470-9.
- Honorary Members of IAPT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2016-12-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18).
- Honors & Awards. Soundings. Fall 2002 [2016-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8).
- Hornstein, Norbert. Minimalist Program.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21-08-13]. ISBN 978-0-19-513977-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8).
- Horowitz, David. The Sick Mind of Noam Chomsky. Salon. 2001-09-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06).
- Hudson, John. Exclusive: After Multiple Denials, CIA Admits to Snooping on Noam Chomsky. Foreign Policy. 2013-08-13 [2016-12-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1).
- Huxley, John. Sydney Peace Prize goes to Chomsk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1-06-02 [2015-12-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4).
- IEEE Computer Society Magazine Hono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ders. Digital Journal. 2011-08-24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3-31).
- Interview: Noam Chomsky Speaks Out On Education and Power. Soundtracksforthem. 2005-09-20 [2016-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5-13).
- Israel: Chomsky ban 'big mistake'. Al Jazeera. 2010-05-20 [2016-05-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14).
- IWW Biography.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2016-05-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17).
- Jaggi, Maya. Conscience of a nation. The Guardian. 2001-01-20 [201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1-11).
- Jamia Millia Islamia named a complex honoring Noam Chomsky. Jamia Millia Islamia. 2007-05-03 [2007-05-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7).
- Kalman, Matthew. Palestinians Divided Over Boycott of Israeli Universiti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4-01-19 [2021-08-13].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6).
- Kay, Jonathan. The Monomania of an Anti-American Prophet. Commentary. 2011-05-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1-07).
- Keller, Katherine. Writer, Creator, Journalist, and Uppity Woman: Ann Nocenti. Sequential Tart. 2007-11-12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04).
- Knight, Chris. Decoding Chomsky: Science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ISBN 978-030022876-2.
- Knight, Chris. When the Pentagon Looked to Chomsky's Linguistics for their Weapons Systems. 3 Quarks Daily. 2018-03-12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5).
- Knuth, Donald. Preface. Selected Papers on Computer Language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2002. ISBN 978-1-57586-381-8.
- Knuth, Donald E. Preface: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language in which I could use a computer programmer's intuition. Selected Papers on Computer Languages. 2003: 1. ISBN 1-57586-382-0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Knuth: Selected Papers on Computer Language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3 [2021-08-13]. ISBN 15758638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
- Koerner, E. F. K. Towards a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Toward a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Selected Essays. John Benjamins. 1978: 21–54.
- Koerner, E. F. K.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 and its historiography: a few critical remarks.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1983, 3 (2): 147–169. doi:10.1016/0271-5309(83)90012-5.
- Lecture 6: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roblem Solving, and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School of Psychology, Massey University. 1996 [2007-09-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1-17).
-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 leafcutter bee Megachile chomskyi from Texas. Pensoft. [2016-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14).
- Lukes, Steven. Chomsky's betrayal of truths (PDF).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THES). 1980-11-07 [2018-03-0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9-04-12) –透過libcom.org.(facsimile copy of Lukes's THES article,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correspondence it provoked, including from Ralph Miliband, Ken Coates and others, with Chomsky's response)
- Lyons, John. Noam Chomsky revi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ISBN 978-0-14-004370-9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MacCorquodale, Kenneth. On Chomsky's review o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January 1970, 13 (1): 83–99. ISSN 0022-5002. PMC 1333660 . doi:10.1901/jeab.1970.13-83.
- Mace, Mikayla. Linguist Noam Chomsky joins University of Arizona faculty. Arizona Daily Star. [2018-07-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7).
- Macintyre, Donald. Chomsky refused entry into West Bank. The Independent. 2010-05-17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12).
- McGilvray, James. Chomsky: Language, Mind, Politics second. Cambridge: Polity. 2014. ISBN 978-0-7456-4989-4.
- McNeill, David. Noam Chomsky: Truth to power. The Japan Times. 2014-02-22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4).
- Milne, Seumas. 'US foreign policy is straight out of the mafia'. The Guardian. 2009-11-07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6).
- Nettelfield, Lara J. Courting Democracy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21-08-13]. ISBN 978-05217638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6).
- Nikolic presented the Sretenje Order Николић уручио Сретењско ордење. Politika. 2015-02-15 [2021-01-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05) (塞爾維亞語).
- Noam Chomsky. MIT Linguistics Program. 2002 [2017-0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17) –透過chomsky.info.
- Noam Chomsky. 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 Biography in Context. Detroit, MI: Gale. 2016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14).
- Noam Chomsky Awarded 2011 US Peace Prize. US Memorial Peace Foundation. [2020-0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9).
- Noam Chomsky Joins NAPF Advisory Council. 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 2014-03-01 [2018-07-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5).
- Noam Chomsky on Life & Love: Still Going at 86, Renowned Dissident is Newly Married. Democracy Now!. 2015-03-03 [2016-05-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10).
- O'Grady, Cathleen. MIT claims to have found a "language universal" that ties all languages together. Ars Technica. 2015-06-08 [2021-08-13]. doi:10.1073/pnas.15021341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5).
- The one hundred most influential works in cognitive science. Center for Cognitive Sciences,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2015-11-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6).
- Ortiz, Aimee. Chomsky joins University of Arizona faculty. The Boston Globe. 2017-08-28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2-20).
- Otero, Carlos Peregrín. Editor's notes to Selection 4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mind"). Chomsky on Democracy & Education. By Chomsky, Noam. . Otero, Carlos Peregrín (編). Psychology Press. 2003: 416 [2021-08-13]. ISBN 978-04159263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8).
- Páez, Nadia. Systematics of Huicundomantis, a new subgenus of Pristimantis (Anura, Strabomantidae) with extraordinary cryptic diversity and eleven new species. ZooKeys. 2019, (868): 1–112. ISSN 1313-2970. PMC 6687670 . PMID 31406482. doi:10.3897/zookeys.868.26766 .
- Partee, Barbara H. Asking What a Meaning Does: David Lewis's Contribution to Semantics. Loewer, Barry; Schaffer, Jonathan (編). A Companion to David Lewis.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5 [2021-08-13]. ISBN 978-111838818-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6).
- Persson, Ingmar; LaFollette, Hugh (編). The Blackwell Guide to Ethical Theory 2nd. John Wiley & Sons. 2013. ISBN 978-1-118-51426-9.
- Pilkington, Ed. Noam Chomsky barred by Israelis from lecturing in Palestinian West Bank. The Guardian. 2010-05-16 [2016-05-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7).
- Press release: Séan MacBride Peace Prize 2017 (PDF). Berlin: 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 2017-09-06 [2017-12-09].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2-25).
- Prickett, Stephen. Narrative, Religion and Science: Fundamentalism Versus Irony, 1700–19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4. ISBN 978-0-521-00983-6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Prospect/FP Top 100 Public Intellectuals Results. Foreign Policy. 2005-10-15 [2015-1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5-10-25).
- Pullum, Geoffrey; Scholz, Barbara.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stimulus poverty arguments (PDF). The Linguistic Review. 2002, 18 (1–2): 9–50 [2021-08-13]. S2CID 143735248. doi:10.1515/tlir.19.1-2.9.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2-03).
- Rabbani, Mouin. Reflections on a Lifetime of Engagement with Zionism, the Palestine Ques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A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012, 41 (3): 92–120. doi:10.1525/jps.2012.XLI.3.9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8-03).
- Radick, Gregory. The Simian Tongue: The Long Debate about Animal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ISBN 978-022670224-7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Rai, Milan. Chomsky's Politics. Verso. 1995. ISBN 978-1-85984-011-5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Robinson, Paul. The Chomsky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1979-02-25 [2021-08-13].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23).
- Rohrmeier, Martin. Spyridis, Georgaki; Kouroupetroglou, Anagnostopoulou , 編. A generative grammar approach to diatonic harmonic structure (PDF). Proceedings of the 4th Sound and Music Computing Conference. 2007: 97–100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08-14).
- Ruiter, J. P. de; Levinson, Stephen C. A biological infrastructure for communication underlies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languag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October 2010, 31 (5): 518. ISSN 1469-1825. doi:10.1017/S0140525X08005086.
- SASA Member. Serb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2003-10-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 Searle, John R. A Special Supplement: Chomsky's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72-06-29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3-21).
- Sengupta, Kim.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alarm the West by backing Islamist extremists the Americans had bombed in Syria. The Independent. 2015-05-12 [2021-08-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5-13).
- Seuren, Pieter A. M. Western linguistic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1998. ISBN 0-631-20891-7.
- Sipser, Michae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Computation. PWS Publishing. 1997. ISBN 978-0-534-94728-6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Slife, Brent D. Time and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The Spectacle of Spain's Tourist Boom and the Reinvention of Difference. SUNY Press. 1993: 115. ISBN 978-0-7914-1469-9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Smith, Neil.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5. ISBN 978-052154688-1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大陸譯版見:史密斯, 尼爾. 乔姆斯基:思想与理想. 由田啟林; 馬軍軍; 蔡激浪翻譯 第2版.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1-11-21]. ISBN 978730020555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1).
- Soderqvist, Thomas. Science as Autobiography: The Troubled Life of Niels Jer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4. ISBN 978-0-300-09441-1.
- Sperlich, Wolfgang B. Noam Chomsky. Reaktion Books. 2006. ISBN 978-1-86189-269-0 –透過Internet Archive.
- 大陸譯版見:斯波里奇, 沃夫岡·B. 乔姆斯基. 由何宏華翻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2022-03-25]. ISBN 978-7-30117-03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31).
- Steedman, Mark J. A Generative Grammar for Jazz Chord Sequences. Music Perception. 1984-10-01, 2 (1): 52–77. JSTOR 40285282. doi:10.2307/40285282.
- Swartz, Aaron. The Book That Changed My Life. Raw Thought. 2006-05-15 [2014-01-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17).
- Szabó, Zoltán Gendler. Chomsky, Noam Avram (1928–). Shook, John R. (編).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American Philosophers. Continuum. 2010 [2021-08-13]. ISBN 978-0-19-975466-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7).
- Tanenhaus, Sam. Noam Chomsky and the Bicycle Theory. The New York Times. 2016-10-31 [2016-10-31].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18).
- Thornbury, Scott. An A–Z of ELT (Methodology). Oxford: Macmillan Education. 2006: 234. ISBN 978-140507063-8.
- Tomasello, Michael. Language is not an instinct. Cognitive Development. January 1995, 10 (1): 131–156. ISSN 0885-2014. doi:10.1016/0885-2014(95)90021-7.
- Tomasello, Michael.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978-0-674-01030-7.
- Tomasello, Michael. Universal grammar is dea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October 2009, 32 (5): 470–471. ISSN 1469-1825. S2CID 144188188. doi:10.1017/S0140525X09990744.
- Tool Module: 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 The Brain From Top To Bottom. McGill University. [2015-12-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9-10).
- Tymoczko, Tom; Henle, Jim. Sweet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Modern Logic.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4-04-08: 101 [2021-02-26]. ISBN 978-0-387-9893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8).
- U.S., Britain ignored 'culture of terrorism': Chomsky. The Hindu. 2001-11-04 [2016-03-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2-24).
- Viggo Mortensen's Spoken Word & Music CDs. [2016-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12-15).
- Vučić, Nikola. Noam Chomsky potpisao Deklaraciju o zajedničkom jeziku [諾姆·杭士基已簽署《通用語言宣言》]. Sarajevo: N1. 2018-03-27 [2018-06-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5-01)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 Weaver, Matthew. Chomsky hits back at Erdoğan, accusing him of double standards on terrorism. The Guardian. 2016-01-14 [2016-0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13).
- Weidenfeld, Lisa. Noam Chomsky Is Leaving MIT for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Boston Magazine. 2017-08-29 [2019-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7).
Chomsky has been at MIT since 1955, and retired in 2002.
- Weiner, Tim. The C.I.A.'s most Important Mission: Itself. The New York Times. 1995-12-10 [2021-08-13].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10).
- Younge, Gary; Hogue, Kat Keene. Noam Chomsky: 'The Occupy movement just lit a spark' – video. The Guardian. 2012-07-06 [2016-04-22]. ISSN 0261-307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16).